



文/康慨
發于2019.6.10總第902期《中國新聞周刊》
巴克夫人的《重生三部曲》是非凡的文學杰作,具備一切達成這一標準的優秀品質。它也遠不止是寫戰爭創傷的戰爭小說和寫心理診療的心理小說。“現代史詩”這頂桂冠如今固然已遭濫用,戴在它頭上卻理所應當。但更令人驚奇的是它制造驚奇的能力。它執意而且樂于打破文體(通過互文)、階級(通過一個成為“臨時紳士”的工人階級子弟)和性(通過大量的交媾場面)的界限或禁忌,顯露出勃勃的雄心和圓熟的技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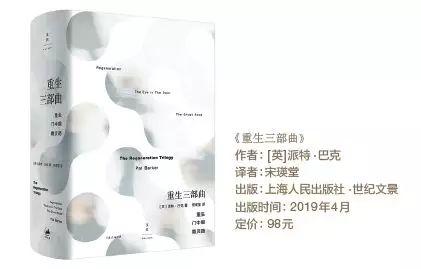
故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詩人和戰斗英雄薩松在公開發表反戰宣言后,被送入蘇格蘭愛丁堡的一座部隊醫院,接受人類學家出身的精神病名醫瑞弗斯的治療。他在這里見到眾多罹患彈陣癥(《不列顛百科全書》已將“彈陣癥”重命名為“戰斗疲勞癥”,更為人所知也更寬泛的概念則是“創傷后應激障礙”)的戰友,其中有晚輩詩人歐文和一位出身低微、拼命打拼才升至軍官階層的普萊爾少尉。薩松幻視,歐文口吃,普萊爾失語。其他人或失憶,或失明,或失聰,或失禁,或嘔吐,或自殘,或行為乖張。每個人都有揮之不去的噩夢。
瑞弗斯形同慈父。他發現,病人從小受環境熏陶,將壓抑情緒視為男性氣概的本質,認為男人如果情緒崩潰或哭泣,或者坦承恐懼,就是娘娘腔,是弱者,是敗將,而不是男子漢。與崇尚強力電擊的同行相比,他毫無帝國軍醫的陽剛之氣,又深受弗洛伊德影響,將話療術付諸實踐。
于是對話連著對話,一場接一場,驅動故事緩慢前行。戰爭若遠若近,恐懼若暗若明,其間點綴著各種形容腐尸、殘肢、血雨、焦骨、體液、嘔吐物、排泄物和夜半尖叫的詞匯。人人受煎熬,苦于理智與情感、良心與職責、記憶與現實的來回撕扯。沒有飛越瘋人院那樣的戲劇性情節,前面幾百頁的鈍刀子割肉,反復激蕩的只是內心的波瀾,如一座座壓抑的記憶火山。然后呢?或可借用魯迅的詩句(盡管語境殊異):“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
薩松、歐文和瑞弗斯在歷史上實有其人,另外幾位患者出自瑞弗斯的病例報告,只是更易了姓名,但普萊爾這個人物多半是作者的創造。普萊爾在三部曲的后兩部《門中眼》和《幽靈路》里晉升為一號主角,也為作者多少卸去一點史實的束縛,打開自由發揮的空間。
薩松重回前線,故事從封閉的醫院移至首都倫敦,底層人民接次登場,語言變得生動鮮活,節奏加快了,情節也明顯更為曲折。“臨時紳士”普萊爾調入軍需部情報處,搞反特工作,調查在押女犯貝蒂·羅珀。她偏巧是他童年時代情同母子的恩人,長期容留反戰分子,向愛爾蘭秘密運送逃兵,并卷入用南美箭毒行刺首相勞合·喬治的離奇密謀。
在瑞弗斯醫生眼里,是政府和國會里的一些人為了達成自己的欲望,把一批批的年輕人送上戰場。戰爭宣傳激發了愛國熱情,繼而導致對和平主義者、良心反戰者、罷工者和少數群體的集體迫害。戰爭部尤其相信同性戀是德國腐蝕英國先進文化、破壞不列顛社會基礎的陰謀,因此大造輿論,羅織“陰蒂崇拜會”等莫須有的罪名,炮制首批四萬五千人的同性戀名單。在前線將士中間,標準而與浪漫無染的同志之情得到高度推崇,反之則被大加撻伐。戰友是最可愛的人,基友則統統該死。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真要同志懷春,便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普萊爾卻來者不拒。他性欲亢進,甘冒種種風險——無論是不保險的保險套,還是群眾的舉報——利用各種機會奮力性交,對象從街頭流鶯到傷殘軍官,從軍火女工到法國少年。但在意外發現出賣童年好友的真兇之后,他重返前線。11月初,戰爭即將結束,歐文在他眼前中彈死去,這是他們的最后一次沖鋒。
凱旋在子夜是集體主義的神話。傳統的戰爭文學用抽象的、豐碑式的社會記憶,代替具體的、創傷性的經驗。雞血戰爭文藝作品更是充斥著對民族主義和男子氣概的過度渲染。但從個人層面上講,巴克告訴我們,戰爭沒有勝利者。薩松說:“我覺得自己從百年后的將來回顧。我好像看見我們的幽靈。”
臺譯本在某種程度上過濾或弱化了原文的色彩,同時帶來了對話中可以感知的另一種漢語口音。除此之外,我對這譯本沒有更多的抱怨。就準確性而言,它當在如今絕大部分同類中譯本的水準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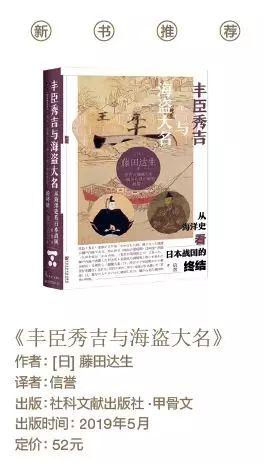
被稱作“倭寇”的日本海盜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日本近世史專家藤田達生從海洋史的角度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他認為,戰國時代的落幕標志著日本歷史上以豐臣秀吉等人為代表的陸地邏輯戰勝了以河野氏、毛利氏等海盜大名為代表的海洋邏輯,直到兩個世紀后日本重新踏上海洋國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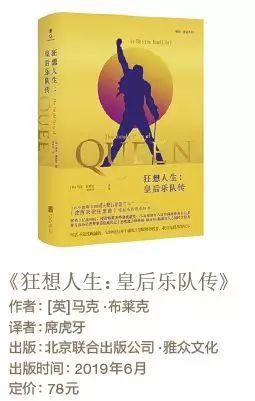
1971 年,當倫敦的四位大學生最終走到一起,流行音樂史上最華麗高貴的樂隊就此誕生。英國著名文化記者馬克·布萊克通過近百次獨家采訪,第一次完整講述了這支不斷創造歷史奇跡的樂隊背后的故事,展示了其成長為世界巨星的全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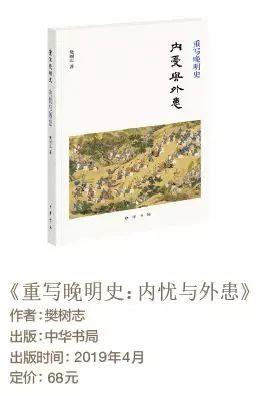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樊樹志新作。面臨內憂與外患的晚明王朝急于求治,卻困于大臣間不斷的黨爭和傾軋。作者站在全球史的高度,在遍閱晚明史料的基礎上,由朝廷間的日常細節建構出晚明大歷史,史識、史見與歷史新知交融筆下。

作者是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五歲時與家人從古巴移居美國紐約。離開故鄉,才識鄉愁。她的多重身份,像一把解密之匙,引領讀者從移民和女性的視角探究古巴猶太世界的歷史變遷以及與西方的關系。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20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